楔子
你好,这里是《文明之旅》。欢迎你,穿越到公元1066年,大宋治平三年,大辽咸雍二年。
这一期,我们继续来聊“濮议”。什么是“濮议”?简单说,就是现在的大宋天子宋英宗,能不能管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叫一声爸爸?他是过继给宋仁宗当儿子,然后才当的皇帝,现在又要回去认亲生父亲,这事儿合适不合适?就这么个事儿,大臣们分成两派,一派是负责日常政务运行的宰相班子,另一派是负责给朝廷提建议的台谏官,这两派发生了激烈争论。这就叫“濮议”。
到了1066年的2月,争论已经持续了二十个月,突然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:仁宗的皇后、现在的曹太后出手了。她从宫里面递出来一张纸条子,说这事我就做主了:就让皇帝管濮王叫亲爹,尊濮王为皇帝吧!你看,曹太后不仅同意英宗管濮王叫爹,还送了一个顺水人情,说你还可以追封你爹为皇帝。
请注意,仅仅六个月前,曹太后也曾经从宫里面递出一张条子,说,谁提出这么个议题?皇帝管濮王叫爹?荒唐!这个题目就不该提出来!把宰相数落了一顿。
而现在,太后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,这就把所有的濮议反对派们给整尴尬了。原本,他们是打着仁宗和曹太后的旗号反对英宗认回亲爹,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欺负太后,对太后不孝。现在好了,曹太后自己出面说可以,你们还能有啥话说?
英宗马上借坡下驴,发布诏书:说我称濮王为亲爹,你们都听好了,这是老太后的意思,我是听她的话才这么办的。不过呢,追尊濮王为皇帝的事,就先算了吧。
当然,濮议的反对派们也没有那么容易就善罢甘休。老太后答应了?会不会是宰相韩琦、欧阳修这些人勾结宦官,给曹太后下了迷魂汤?或者老太后被胁迫的?而且,她是一个女人,又没有垂帘听政,这条子算什么?无效!反对派继续发言,奋勇战斗。
紧接着,大宋历史上一个名场面就诞生了:台谏官几乎被一锅端。
当时台谏官一共是九个人,其中两个是被临时拉上来凑数的,上任还没两个月,他们没有掺和到濮议中,剩下的七个台谏官,在濮议问题上,意见完全一致,都是铁杆反对派。其中,司马光前不久调任了龙图阁学士,没有受到处分。还剩六个人:有三个人,吕诲、范纯仁、吕大防被罢去台谏官职位,外放州县官。还剩的三个人当时正在出使辽朝。过了一个月,等这三人回到开封,说,我们也坚决要和吕诲他们共进退,要走一起走。这是最后还要争一争的姿态。朝廷也没含糊,走就走吧,把这三个人也罢了官,请出了开封。
这可是大宋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儿,因为一场争论,台谏机构几乎被一把清空了。台谏机构是干嘛的?就是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。皇帝拒绝听意见了,那不就是昏君了吗?
你可能会想,一定是英宗本人任性妄为,干出这样不体面的事。慢着。这就多少有点错怪英宗了。我们来看当时的历史记载:当时,当双方争议最激烈的时候,是宰相群体给英宗出了一道单选题,说宰相跟台谏官没法共存,要么宰相走人,要么台谏走人。你看着二选一吧。英宗犹豫了半天,这才做出赶走全部台谏官的决定。英宗还特别嘱咐了一句,对台谏官的惩罚不要太重,差不多得了。
你看,濮议不只是皇帝和台谏官的矛盾。牌桌上还有一拨人,那就是宰相班子,具体说就是宰相韩琦和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。而且,他们才是真正和台谏官撕破脸搞对立的一方。
这就让人奇怪了。韩琦、欧阳修当年可都是做过台谏官的,而且他们后来在士大夫群体中的美誉,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他们直言敢谏。尤其是欧阳修,他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议论。在当时的人看来,他就是宋朝台谏官的宗师,宋朝朝堂上敢于提意见的风气,就是他带出来的。现在,他们两个竟然亲自下场赶走台谏官,这是为啥?
好,这一期,就让我们来解个闷,看看韩琦、欧阳修为什么不惜破坏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直言极谏的传统,也要站到台谏官的对立面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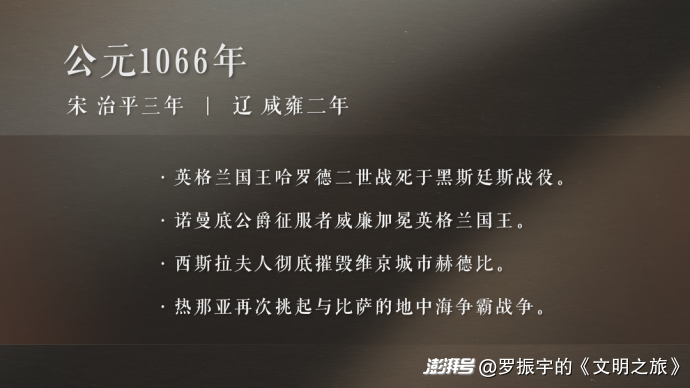
宰相的心事
宰相韩琦和欧阳修,为什么站到了台谏官的对立面?
我们首先排除一个因素:这肯定不是个人恩怨。
从人际关系上说,韩琦、欧阳修原来跟司马光这些台谏官的私交不错的。尤其是欧阳修,岁数资历都摆在那里,他比台谏官这些人都至少大上个十几岁,而且作为文坛盟主,欧阳修又有提携年轻人的习惯,对濮议中的著名反对派,司马光、吕公著这些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推荐之恩。
甚至,像韩琦跟范纯仁之间,那简直是情同骨肉的关系。因为范纯仁是韩琦当年的战友范仲淹的儿子。后来台谏官范纯仁攻击宰相韩琦的时候,韩琦在情感上受不了,他说,“我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,是兄弟般的感情,所以我向来把范纯仁看成是自己的子侄辈的亲人哪。他今天这么恶毒地攻击我,他是怎么忍心的?”
所以你看,濮议闹得那么难看,肯定不是因为个人恩怨。那就还有一个可能:濮议这件事的是非确实非常模糊?两派不过是在非常顽固地各执己见?
但是,我读这段史料,有一个强烈的感觉:除了宰相班子里的几个人,韩琦和欧阳修,整个朝野上下的意见非常统一,几乎全都是濮议的反对派。我们今天虽然不再关注濮议中的是非问题,但是在当时,这个是非还是有共识的。
怎么见得这就是“共识”呢?我举个两个侧面的证据。
一个是苏轼的态度。你想,苏轼和欧阳修是什么关系?那是门生和老师的关系啊。欧阳修是对苏轼不遗余力地提携,甚至是要把文坛盟主的衣钵传给他的人。所以苏轼一生都对欧阳修感恩戴德。但是苏轼对濮议是什么态度呢?
这一年的苏轼,因为父亲苏洵去世,他要回四川守孝,所以没有直接参与濮议的辩论。但是,三年之后,苏轼在一封奏疏中,还是间接表明了态度:“濮议期间的是非是有公论的,台谏官是为公论而争。”苏轼说这番话的时候,已经是宋神宗的熙宁二年,濮议的风波已经过去,而且欧阳修也还健在。他能这么说,可见濮议的是非,当时是有共识的。苏轼也不能瞪眼说瞎话。
我还有一个侧面的证据,来自司马光。司马光是濮议中的第一个反对派。但是,在濮议的过程中,他调离了谏官的岗位,所以,后来台谏官全体被赶出开封的时候,他既没有发言的责任,也没有共进退的义务。但是,司马光事后还是几次上书,要求朝廷把自己也罢黜了。司马光是这么说的:我是濮议最初的反对派,现在就留我一个人在开封待着,我实在是没脸见人。我现在白天也吃不下饭,晚上也睡不着觉,进办公室,看见人我就惭愧,出门,遇到路上的人我也是惭愧。我也算是一个珍惜名节的人,这么被人戳脊梁骨,我是连人都做不成了。你们还是赶紧把我贬谪了吧。
你听听,到了这个时候,他争的已经不是事情本身的是非了。而是:如果我不和台谏官一起被贬,已经关乎到我立身的名节,我在整个士大夫群体里抬不起头。从司马光感受到的压力来看,濮议的两边阵营,已经不仅是宰相和台谏官了,而是宰相班子和整个士大夫群体了。这也从侧面说明了,在当时士大夫的观念里,濮议的是非是明确的,是有共识的。

说到这里,你会不会觉得奇怪:这韩琦和欧阳修,也是士大夫出身啊,他们和大家也是共享同样的价值观啊,怎么大家都拼命反对的事情,只有他们赞成呢?而且是拼命赞成,毫不退让呢?
如果换了别的人,那也好解释:奸臣呗,为了讨好宋英宗,甘当皇帝的打手,就是想往上爬呗。但他们是韩琦、欧阳修啊,无论是人品还是能力,都是在大风大浪中检验过的。当年庆历新政时期,他们那么年轻,都可以不计个人荣辱,为了自己的信念理想猛打猛冲。现在老了,功成名就、位极人臣,反而会为了讨好皇帝,甘当奸臣,站到天下士大夫的对立面?这个解释说不通吧?
那我们今天就试着提出一个解释,您听听有没有道理?
我们先来看看韩琦和欧阳修现在的角色。韩琦是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、平章事、右仆射、封魏国公,就是首席宰相。而欧阳修是参知政事,是协助宰相处理政务的副宰相。好,我请你设身处地想象,过去几年间,如果你也是大宋朝宰相班子的一员,你的首要的执政目标是什么?
非常清晰:就是完成好政权在两代皇帝之间的过渡。
这个任务非常艰巨。首先,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,这本身就给政权交接带来很大的变数。而且,仁宗在位42年,大多数朝臣这一辈子只知道这么一位皇帝,太习惯了,太有感情了,现在换了新天子,难免有各种不适应。
所以,过去几年,你真是操不完的心:你先是得不断地跟仁宗较劲,劝他立皇子;接下来,仁宗去世,你得护着英宗顺利当上皇帝;英宗继位以后就生病,你得一边请曹太后出来垂帘听政,一边又得想着及时让曹太后还政。
说到曹太后,这里面其实还有几个非常凶险的时刻。
上一期节目,我们说过一个非常蹊跷的事:有个宫女为了少几顿打,多吃点好吃的,就诈称怀了仁宗的龙种。如果这是真的呢?如果她真的为仁宗生了一个男孩,一个遗腹子呢?会不会威胁到英宗的皇位?不知道。但事实是:曹太后把这件事瞒得严严实实,好吃好喝养着这个宫女,直到事情败露。你说太后这是想干嘛?真的说不好啊。
还有,曹太后曾经派人给宰相韩琦带了封信,信里记的都是英宗在后宫犯的过错,这是在宰相面前告皇帝的状啊。韩琦怎么处理的?韩琦当着使者的面,就把信烧了,然后对使者说:“请你回去禀报太后,皇帝生病了嘛,言语行为有点过失,很正常,不足为怪啊。”
还有一回,曹太后问宰相,说汉朝的昌邑王是怎么一回事啊?这句话一出口,那真是晴天霹雳。昌邑王是谁?是汉朝被废掉的皇帝。曹太后问这个问题,用意非常明显,就是试探宰相的口风,看有没有可能把英宗废了。这是电光石火的瞬间,宰相只要略作犹疑,下面事态的发展就不好说了。韩琦先是装傻充愣,就反问曹太后,汉朝的昌邑王有两代呀 ,您指的是哪位?曹太后马上就清楚韩琦的意图了,也就不说话了。韩琦乘胜追击,反问太后:这事您听谁说的呀?曹太后慌了神,赶紧说,我只是老早听过这么一耳朵,什么意思都没有哈。
过了一些日子,曹太后又来了,说我昨天做了个梦,梦到英宗在庆宁宫,大孙子倒是骑着龙上了天。这个庆宁宫,是英宗做皇子时候的住所。这其实是曹太后在暗示宰相,能不能让英宗退位,让他的长子,也就是未来的神宗提前即位。宰相韩琦听了以后,继续装傻充愣,说英宗要是回原来的住所,可能是他身体康复的征兆,哎呀,这个梦做得好!
你可能会说,这老太太要干嘛呀?不就是和英宗闹点矛盾吗?至于天天琢磨着废掉他吗?
不能这么说。英宗当时病了,而且很明显是精神性的症状,不认识人,而且胡言乱语嘛,这种情况下,曹太后作为仁宗的遗孀,为老赵家的花花江山着想,想换个合适皇帝,或者至少做一点准备,不能说是出于私心。
但宰相为什么又坚决不能同意呢?对于皇权政治来说,最重要的是什么?不是皇帝本身的能力,而是皇位的合法性。皇帝有合法性,就能给天下稳定的预期,政权就能稳定运行。如果以皇帝生病或者没有执政能力不行为由换皇帝,那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,甚至是打开了一个魔鬼的盒子,以后的野心家可就多了一个篡位的理由。所以对于宰相来说,这个时候,一动不如一静。既然英宗已经是合法的皇帝,那就要尽可能保住英宗。
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,选贤任能好像是天经地义的,但是在古代社会不是这样。商朝的继位原则是兄终弟及,而周朝改成了父死子继,而且是嫡长子继承。王国维先生在《殷周制度论》里说,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创新。为什么?万一嫡长子是个傻子,或者不如其他人贤能,为什么还要让他继承王位呢?王国维先生解释:因为对天下来说,最大的好处是安定,最大的坏处是纷争。嫡长子继承,虽然可能继位的是个傻子呆子,但那毕竟也是老天定的,就是他了,没什么好争的。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利益。
理解了这个原理,你就明白宰相班子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使命了:必须要想方设法维护英宗的皇位。不仅要让他坐得住,还要让他坐得稳;不仅要坐得稳,还要帮助他树立权威。扶上马,还要送一程。
所以,如果这个时候英宗和曹太后发生了任何意见分歧,宰相们没有选择,必须站在皇帝这一边。甚至,甚至当英宗有点理亏的时候,也不得不这么做。
我们可以大致推想一下事情发展的逻辑:
刚开始,可能只是英宗本人露出了想认濮王这个亲爹的想法。宰相当然知道英宗这个心结的来历,你如果感兴趣,可以看我们《文明之旅》的1065期的节目。清官难断家务事,既然英宗受伤那么深,那就迁就他一下吧,心结一解,他才可能回到正常状态,国家机器才能顺利运转。接下来,宰相就放了个气球去试探各个方面的反应。结果发现士大夫群体,尤其是台谏官群体坚决反对,那就回来自己找理论依据。班子里不是有欧阳修这个大理论家吗?来,你去找儒家原典里的理论依据。这种事,如果非要找,那还能找不着吗?于是欧阳修就开始下场辩论。最后一发而不可收。
那你可能会问,宰相既然遇到了坚决的反对,那就退回来,不行吗?为什么一定要死扛到底呢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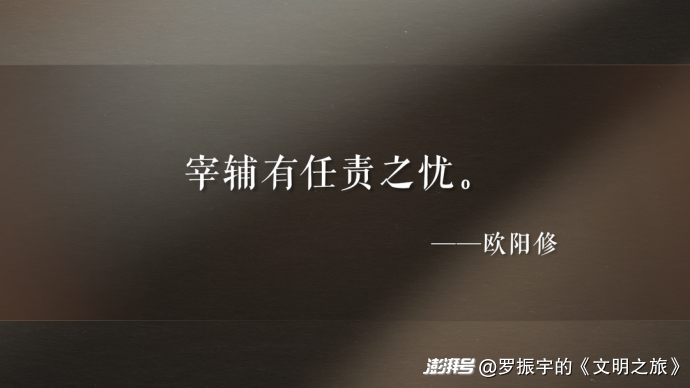
皇帝的权威
濮议一旦开始,对立双方的阵营一旦成型,宰相班子最大的难处在于:他们没有办法退让。因为如果承认英宗认亲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,马上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。
首先是皇帝的权威受到了打击。
你可能会说:啊?权威至于那么脆弱吗?认个错,就会被削弱?如果是已经建立的权威,当然不至于。比如宋仁宗,怎么从善如流,知错能改都没问题。反而会赢得美名。可是,如果是正在建立的权威,就不行了。
什么是“权”?《说文解字》里有个解释,说权的意思是“反常”,是不是挺奇怪的?在古代,“权”有一个相对应的词,叫“经”。经是什么?是织布的经线,经线,那是定框架,定规矩的。引申出来有个词叫“守经”。什么时候要“守经”?就是需要按规定来的时候。那什么时候“行权”,那就是不按规矩,或者没有规矩的时候,这就叫反常。
比如一家公司,什么人能进公司大门,平时按制度来就行,有门卡就进,没有门卡就不让进。这就叫“守经”。但是,这个时候有个特殊的人,没有门卡也要进,怎么办?保安只好请示上级,请他来决定:在制度没有规定,或者违反制度的情况下该怎么办?这就是“行权”。一言以蔽之,权力就诞生在没有制度、没有规矩的地方。
所以,自古以来,建立权威的一个办法,就是制造一个和正常是非、正常逻辑相反的场景,然后用权力来扭曲现实。比如,秦国搞变法的时候,商鞅为什么要“徙木立信”啊?搬一根木头怎么可能值那么多钱?但是商鞅很反常地给了,所以权威建立了。还有,秦朝的赵高,能够反常地逼着你指着一头鹿叫马,他的权威就建立了。

所以,如果宋英宗的这个想法一露头就被否决,这是对他的权威的沉重打击。
后果还不仅于此。更重要的是,濮议的实质,是在英宗和仁宗、曹太后之间评是非,如果英宗输了这一局,曹太后又燃起了废立皇帝的心思,那就为英宗又添了一条必须下台的理由,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这更是宰相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结局。
说到这儿,你心里可能又升起一个疑问:那是非呢?你韩琦和欧阳修,可是标准的儒家士大夫啊,如果你们内心里不认同英宗的这个想法,为什么在行动上还要支持呢?难道只讲利弊,就不讲是非了吗?
这没有办法。只要你是一个要对结果负责的人,只要你有明确且具体的行动目标,你有时候就不得不让是非问题暂时靠边站。
我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:你孩子明天就要高考,今天犯了个小错误,你非得今天晚上就要跟他争出个子丑寅卯,让他道歉认错吗?不会吧?你肯定说,“没事没事,这事不重要。明天好好考试要紧。”那你是没有是非的人吗?不。你只是有更紧急的目标而已。
你中午在办公室为一个问题和同事争得面红耳赤,下午发现你的客户在这个问题上也和你意见相反,你也会和客户争得面红耳赤吗?不会吧?那你是没有是非的人吗?不。拿下当前这个客户的单子更加重要而已。
回到濮议:宰相这一方,既然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帮助英宗迅速地建立权威,完成新老两代皇帝的顺利过渡,那么,濮议本身的是非,确实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这也符合双方的论战风格。争议的过程中,很明显,宰相群体的目标不是要吵赢这场架,而是赶紧结束这场吵架。
宰相这边韩琦和欧阳修加起来,正面论述观点的文章只有四篇。而看反对派那边,可以说是连篇累牍,仅仅吕诲一个人,就写了26篇奏疏。
欧阳修是宰相班子的文胆,主要理论论述靠他。但是他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呢?有一个记载说,欧阳修原本是不知道怎么替英宗说话的。但是有一天,他偶然散步到自家小孩子读书的院子,看到桌上有一本《仪礼》,随手翻了翻,找到了一句话。得了,就是它了。就拿这句话当依据去辩论吧。实际上,在此之前欧阳修这辈子都没怎么读过《仪礼》。你看,这是先有论点,再找论据啊。
其实,细看史料,濮议中所谓的论战,宰相这边主要的手段不是争吵,而是不吱声,任你怎么说,不理睬、不回应、不接招。那是真不想恋战啊。
到了后期,宰相这边一看,争是争不出个结果,就赶紧想办法搬出曹太后,想用老太太的一张条子解决问题。这也是想快刀斩乱麻,赶紧收场的迹象。再到后来,英宗决定撵走所有的台谏官,这里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。
在台谏官中,吕诲官职最高,是御史台的副长官,按照制度,要罢免他,朝廷不但要给他一份罢官的圣旨,还得再给一份官告,就是朝廷委任官员的凭证,上面会以皇帝的口吻说明这次任免的理由。但是,当时有规定,如果起草的人,就是知制诰觉得这份命令不妥,是可以拒绝起草的。朝廷非常担心发生这种事,怕节外生枝,干脆把这个制度环节给省了,直接派人把罢官的圣旨送到吕诲家里,收拾收拾,赶紧走人吧。当时的知制诰知道了以后,愤怒之极,说哪有这么干的?还能这么破坏朝廷的制度?
那你说,宰相们不知道这么破坏制度的后果吗?当然知道。韩琦和欧阳修是什么人?典章制度烂熟于胸的人,也是极力维护大宋朝祖宗之法的人。但是有句话叫“事急从权”,当务之急是赶紧结束这场争议,让这几个杠头赶紧走人。制度破坏了,以后再想办法修补吧。
果然,这一年四月四号,刚把所有台谏官赶走,四月十六号,英宗就发布了诏书,说,来呀,天下如果有不公平的冤狱,有不合适的征调,有贫苦的老百姓,各个地方官赶紧去解决。有什么重要的治国建议赶紧提。
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姿态。从这份诏书的口气,你都能感觉得到,宰相们终于松了一口气:吵了快两年的濮议终于结束了,来来来,我们来办点正经事儿吧。
这是我们对宰相这边态度的梳理:为了做好两代君主的顺利过渡,为了大宋朝这艘大船迅速驶进正确的航道,一不小心卷入了一场既赢不了,但也不能输的论战。所谓“做了过河卒子,只能拼命向前”啊。
说完了宰相,一只巴掌拍不响啊,我们再花点时间看看台谏官这边,他们又为什么不能妥协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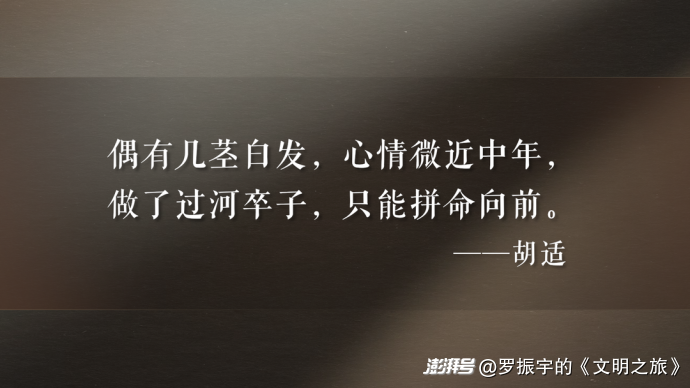
谏官的执拗
濮议当中,台谏官的表现是非常激烈的。
刚开始,争的是那个理儿。你看司马光最初那几封奏疏,写得入情入理。
但是很快,舆论就升级了:大家不再就事论事,而是把矛头指向人。观点的不同被看成是君子、小人、忠臣、奸党的区分。
既然论战双方是君子和小人,那不好意思,这是势不两立的关系,态势于是继续升级:他们把韩琦比作是历史上的各种奸臣,说欧阳修的话就更难听了,说欧阳修“豺狼当路,击逐宜先;奸邪在朝,弹劾敢后?”他就是豺狼,就是奸邪,兄弟们,并着肩地、争先恐后地去弹劾他啊。
有句话说得好,“冤枉你的人,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” ,韩琦和欧阳修是不是奸臣,当时朝堂上的同僚们心里肯定清楚。但是论战一起,唯一重要的是似乎就是输赢,至于用词是不是过分就管不了那么多了。
这一轮攻击无效,论战于是继续升级:既然不听我们的,那我们不干了,把任命书还给你,我们回家把门一关,等着朝廷来处理吧。这就是拿辞职做要挟了。事情到了这一步,终于逼得英宗不得不在宰相和台谏之间做艰难的选择,最后是台谏官全部被贬。
回溯这个过程,你也看得出来,台谏官始终是激化矛盾、推动局势升级的一方。问题是,他们为什么这么做?
要解释这个现象,就必须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。
在我们的印象中,中国一直有鼓励自下而上提意见的政治传统。传说在尧舜的时候,就有“谏鼓”、“谤木”嘛。现在北京天安门前面的那一对华表,也是由谤木演化来的。你要是对君王有意见,你就去他家门口敲鼓,或者在谤木上写字。君王就能听到、看到了。而且,我们还有一大堆君王纳谏的小故事,以及“防民之口、甚于防川”之类的政治格言。

但这只是一个方面。我们还有另一个传统,就是强调说话要符合等级和秩序。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”,你不在那个位置上,就别操那个心。这是孔子说的话,到了孟子的时候,说得就更明确,“位卑而言高,罪也”。你没到那个位置,就说那个位置上的话,这是罪过。这话虽不好听,但也符合我们的朴素直觉:不在那个位置上的人,说的话,既说不到点儿上,往往也不负责任。
你看,这两个传统都有一定道理:一方面,君主要广泛地听意见,另一方面,提意见的人,最好是特定位置、特定身份的人,不能任由所有人不负责任地乱说。矛盾吗?有点矛盾。怎么办?
最后想到的办法是,干脆专门设立一个谏官的职位。在这个职位上的人,可以自由发言,什么都能说,怎么说都行。这套谏官制度是在唐朝才成熟的。主要是两个办法:第一,任用低级官员做谏官。年轻,而且官小,提意见的时候顾虑就少。第二是所谓的“风闻言事”,你听见了就可以说出来,不用给证据,而且言者无罪。这样,谏官的自由度就有保证了。
但是请注意,只有谏官可以这么发言。举个例子,唐朝的白居易,年轻的时候就当了谏官,说话又多又直,经常搞的皇帝非常不高兴,说,“这小子,是我提拔的他,他怎么对朕这么无礼?”但是没办法啊,他是谏官,按规定就是可以说。后来,白居易不当谏官了,但还是改不了这么说话的习惯,这回好了,宰相随便抓了个小事,“该你说吗你就说?”就把他给贬了。所以,白居易因为说话被贬为江州司马,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,别误会,不是什么朝廷拒谏,不是因为他说话的内容不对,而是因为他说话的位置不对。
但你意识到没有?这种谏官制度有一个天然的问题:如果我是谏官,我没有任何具体的职守,不用对任何结果负责,我只负责说话,如果我还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,那会发生什么?我会把我说的话当做工作对象。第一句话出口之后,我下一句话就是为了捍卫第一句话的正确性。第一句话没有奏效,我下一句话就要加强力度以便让它奏效。这是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车。只能往上飙速度、上强度。
比如说,宋朝庆历年间有一个大臣叫石介,他还算是范仲淹、韩琦、欧阳修搞庆历新政时候的战友,性格比较偏激。有人推荐他做谏官。仁宗吓得直摆手,不行不行,他要是当了谏官,我不听他的话,他还不得一头碰死在我这台阶上?千万不要小看一个人捍卫自己的言论的意志。为什么谏官的言论总是会倾向于越来越激烈,总是会迅速地推动态势升级?就是这个原因。
言论,本来是为人的现实目的服务的。人只要有现实目的,言论就会多多少少受到约束。夸大其词、哗众取宠、言过其实,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这个道理,我们小时候听过“狼来了”的故事之后就全懂了。但是谏官呢,没有具体的现实目的,他们就只把论战输赢本身当做目的。这样的言论就很难不扭曲了。
美国经济学家索维尔有一本神作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。他所谓的知识分子,不是指工程师、医生这些人,而是作家、评论家,这些以理念为工作对象的人。工程师的工作做得好不好,自有事实来校准。你建造的桥塌了,不好意思,你得去坐牢。但是以理念为工作对象的人,就麻烦了,理念世界里没有校准工具,他说错了也不用负责。书里有一句非常毒舌的话:“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,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,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。”他这说的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。
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,你在台谏官身上是不是也能看到点他们的影子?他们说欧阳修是豺狼,是奸邪,这是个理念世界的事儿,既无须证据,也没法验证,那可不就怎么痛快怎么说,怎么能赢怎么说呗。而且,这样的言论走在持续强化的单行道上,一旦开始升级,就无法妥协了。
今天,我们分析了濮议双方为什么互不退让的原因。表面看起来,是双方观点不同,但是深究之后你会发现,这其实是两拨人在完全不同的行动依据下发生的对峙。
台谏官是负责说话的人,他们的行动依据是“是非”,所以认准了道理就不退缩;而宰相群体是做事的人,他们的行动依据是“主次”。他们有具体的执政目标,要保证两代皇帝顺利过渡,所以不能在道理上纠缠,要确保大宋朝这艘船能行驶在稳定的航道上。在做事的人看来,是非不是不重要,但是要根据眼前的目标来调整处理的优先级。这其实就是《大学》里说的,“物有本末,事有终始。知所先后,则近道矣。”所谓的做事情能力,不过就是随时随地能分得清楚做事的主次、轻重、缓急嘛。
那你说,隔了这将近一千年,濮议的僵局到底能不能破解?其实用不了一千年,只隔了一百多年,南宋的朱熹就把这个局看得明明白白了。他说,欧阳修肯定是不对,但是那帮台谏官也说得太偏激了。不就是英宗想给他亲爹一点特殊待遇吗?好办啊。给发明一个新称呼不就得了?比如给濮王加个封号叫“太王”不就行了?台谏官非要咬死了只能称“皇伯”,那这个皇伯和其他皇伯还是区分不开啊。你们一步不退,这个事才僵住了嘛。
你看,如果双方真要解决问题,其实有的是办法。可惜,身在这一年的对峙双方,他们都只要赢,所以才和那么多解决方案失之交臂啊。
最后说一个我最近听到的小段子。
话说某村里有个女子。村口的老太太都说她不正经。证据是什么呢?因为所有人都发现,这女子每天晚上都是由不同的男人开着不同的车送回家的。你看,是不是铁证如山?哪有正经女子这么干的?后来村里有一小男孩没忍住,跑去问这个女子,说姐姐,他们都说你不正经,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男人开车送你回家?这女子想了想说:有没有一种可能,这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“滴滴打车”?
你看,一个人看到的铁板钉钉的事实,加上他脑子里的理念,得出的确凿的、深信不疑的结论,能有多荒谬。你别笑,它就是在提醒我们注意,要警惕自己深信不疑的那些理念,也要警惕那些只负责说话的人。
好,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发生在公元1066年的濮议故事。我们下一年,公元1067年再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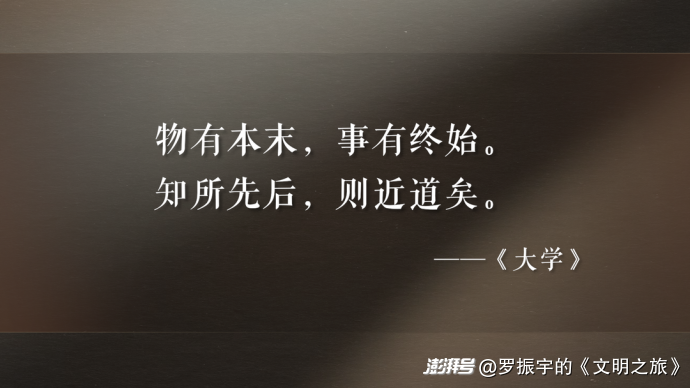
致敬
《文明之旅》1066年,我想致敬一份中国人的行动指南。就是清代朱柏庐写给后代子孙的《朱子家训》。你别看中国古代传下来的家训不少,但最普及的,其实是这个版本。你肯定听过那句: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嘛。
朱柏庐好像也不是很有名,为啥他的这份家训这么出名呢?不光是因为篇幅小,只有500来字,更重要的是,它不是祖宗给儿孙讲空泛的大道理,而是给出明确的行动指南。
你就说开头的这一句:
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,要内外整洁;既昏便息,关锁门户,必亲自检点。
说啥道理了呢?没有啊,清早怎么打扫卫生,黄昏怎么关门闭户,又简单,又明确。但你说,一个人,一个家,在这样日常的规范中坚持,是不是就能变得更好?
咱们再一起学习几条——
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
勿贪意外之财,勿饮过量之酒。
与肩挑贸易,毋占便宜;见贫苦亲邻,须加温恤。
嫁女择佳婿,毋索重聘;娶媳求淑女,勿计厚奁。
家门和顺,虽饔飧不继,亦有馀欢;国课早完,即囊橐无馀,自得至乐。
你看,这些行动指南,我们今天也受用。其实儒家主张哪是那些抽象的道理,都是日用行动的指引。致敬中华文明中重视行动,重视人的行为在细枝末节处的修正意识。
参考文献:
(宋)李焘撰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,中华书局,2004年。
(元)脱脱等撰:《宋史》,中华书局,1985年。
(后晋)刘昫等撰:《旧唐书》,中华书局,1975年。
(宋)欧阳修著,李逸安点校:《欧阳修全集》,中华书局,2001年。
(宋)田况撰,张其凡点校:《儒林公议》,中华书局,2017年。
(宋)叶适:《习学记言序目》,中华书局,1977年。
(宋)叶适撰,王廷洽整理:《习学记言》,大象出版社,2019年。
(宋)罗大经撰,王瑞来点校:《鹤林玉露》,中华书局,1983年。
(清)毕沅撰:《续资治通鉴》,中华书局,1957年。
(清)王夫之著,舒士彦点校:《宋论》,中华书局,1964年。
贾玉英:《宋代监察制度》,河南大学出版社,1996年。
刁忠民:《宋代台谏制度研究》,巴蜀书社,1999年。
虞云国:《宋代台谏制度研究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9年。
晁中辰:《中国谏议制度史》,中华书局,2015年。
赵冬梅:《大宋之变,1063-1086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20年。
王启玮:《言以行道:庆历士大夫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24年。
[美]托马斯·索维尔著,张亚月等译: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,中信出版社,2013年。
赵映诚:《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,2000年第3期。
张贵:《宋仁宗朝谏官活动与怪奇文风研究》,《求是学刊》2015年第2期。
李昌舒:《北宋士人的“好议”之风及其消极影响——以欧阳修为个案的研究》,河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8年第4期。
顾友泽:《欧阳修与濮议之争新论》,《湖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,2024年第6期。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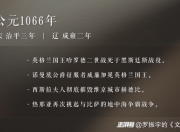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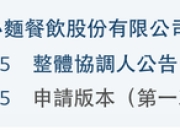




发表评论